【1959年11月2日上午】“陈老总回来了!”黄大娘在田埂上扯着嗓子喊。话音落下,齐刷刷的目光投向那辆刚停下的吉普。
那年秋粮已入仓,亩产报表写得喜人,实际却是“高产田”里稀稀拉拉几株玉米。陈毅跨下车,顾不得擦鞋上的尘土,向田头走。他十岁以前一直在乐至县长大,对这块土壤的气味太熟悉,一口气就能说出哪片坡地的红苕最甜。可此刻,他看到的是大片浮肿的脸庞。

乡亲们还是热情,公社择了最壮的黑猪,开了三口大锅,说要给老总压惊。陈毅摇头,钻进劳作的人群。平日寡言的张茜这次跟着下地,心里直嘀咕:老陈又要折腾。果然,他伸手向一位佝偻的老人讨吃的,“给我一块红苕解馋行不?”老人愣了下,掂量竹篓,只剩三块,还是递了最大那块。陈毅三口两口吞下,又要第二块。张茜轻声提醒:“那是人家午饭。”陈毅脸色沉下来,没有接口。
回公社的土路上,枯草被鞋底踩得吱吱响。县里、区里、省里三个干部陪在左右,他忽然开腔:“吃饭不要钱,真能让乡亲不挨饿吗?”区干部抢先回答:“人民公社一大二公,保证温饱!”县干部紧跟:“今年上交任务超额完成……”省里那位只干笑。陈毅停步,指向不远处又饿又肿的老人,“这样的午餐你们吃得下?浮肿怎么治?医生不行,就得中央开药方!”声音不高,却压得几人汗噗噗往下冒。那顿酒席被他改成百姓加餐,猪肉切得极薄,仍被抢空。
夜里办文艺晚会,戏是独幕《旅客之家》。台上那个自以为高等的“陈同志”耍官腔,刁难服务员,台下哄笑。县领导脸抽搐:老总台下坐着呢!演完,他忐忑去请示,陈毅却和演员一一握手,“演得好,有生活。”他转身对身边人说,这戏里“陈同志”跟我同姓而已,戏是戏,别动不动就上纲上线。说完拍拍乐器箱离场,留下一屋子尴尬。

第二天,乡亲告诉他,新修的小石桥想叫“将军桥”。陈毅摆手,“桥属于劳动人民,何况我不是什么土皇帝,写上‘劳动桥’更合适。”施工木牌随即改字,一旁孩童为“劳动”二字涂上大红漆。
连日忙碌,他始终惦念表弟唐联升。红包封早写好,却迟迟见不到人。有人含糊:“可能出远门了。”陈毅心底犯嘀咕,临赴成都前吩咐亲弟陈季让去打听。结果传来消息:唐联升被划为地主分子,已经关在牛棚。镇干部怕出“政治事故”,硬拦住亲戚相见。

得知真相那晚,陈毅在省招待所拍案而起,“我能和帝国主义谈判,怎么就不能见自己表弟?统战工作若连亲戚都顾不上,那算什么统战!”他语气急促,连说三个“可笑”。停顿片刻,又补一句:“改造地主,关键是改思想,不是让人一辈子抬粪。会写字会算账就让他写,会修水利就让他修,脑力劳动也是劳动。”屋里灯泡嗡嗡响,众人谁也不敢插嘴。
11月下旬,他的公务仍排得满满:视察成昆铁路勘测、听取四川外贸汇报。可在行程表最末一行,他亲手写下:“唐联升进京。”还把那封财神红纸包交给陈季让,“见到人亲手递,告诉他我等他喝茶。”
年底,唐联升获释。凸肚的红苕地里,他攥着那封红包,在家人面前一声不吭地哭了。红包里不过几张钞票,却压着一句话:勤学,勿怠。这六个字他后来抄了四遍,贴在堂屋、牛棚、祠堂和自家书桌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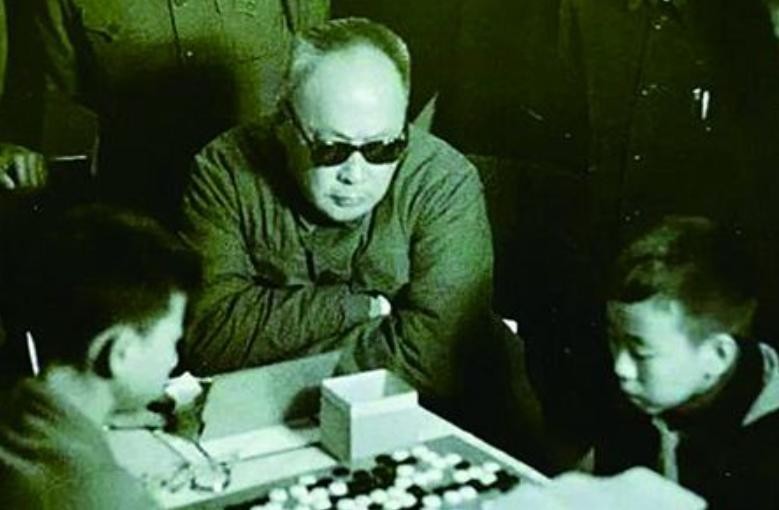
不得不说,陈毅这趟返乡,火气不小,却也让不少人冷静下来。县里很快调整了浮肿病救治方案,公社改口粮分配,戏剧团继续演《旅客之家》还新增角色“周服务员”,桥名“劳动桥”就此沿用。唐联升则被调去县文化站做资料整理,一支毛笔写到晚年,成为当地口碑不错的业余史料专家。
历史没有脚注,却留痕。1959年的乐至县,一块红苕、一通火气、一封红包,把宏观政策与人情冷暖连在一起。许多年后,唐联升谈起那一年,只说一句:“表哥没给我特权,只给了我条活路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