克罗恩病又被称为“绿色癌症”,并非因为它是癌症,而是因其顽固、反复、难治的特性与癌症类似。患者常年腹泻、腹痛、营养不良,生活质量严重下降;发作期频繁如厕,甚至一天十余次,严重影响学习、工作与社交。此外,该病多发于青壮年,无明确根治方法,需终身服药,甚至多次进行手术干预。

1950年,李佃贵出生于河北白洋淀一个世代行医的“渔医”家庭。父亲白日驾着小船行医,夜晚在油灯下抄方研书。芦苇根、荷叶蒂这些看似不起眼的水泽草木,常被他随手采来,煎汤治病。李佃贵年幼时常坐在船尾,看父亲替渔民包扎、熬药、捶背,一股对中医的敬畏与好奇悄悄在心底生长。
7岁那年,李佃贵亲眼目睹邻居家少年因“怪病”暴瘦如柴、腹痛便血,最终不治身亡。那是他第一次面对死亡,也第一次感受到医生的无力。多年后李佃贵回忆起:“那其实是克罗恩病,当时中医称作‘肠澼’。”当时父亲反复翻阅《难经》,其中一句“肠澼下脓血”被朱笔圈了又圈,几乎翻烂。那段悲痛而沉默的记忆,成为他一生投身肠病研究的原点。
1970年,李佃贵考入河北新医大学(今河北中医学院),师从肝病名家刘宪章。求学期间,他跟随老师在太行山区巡诊时,接触到大量久泻不止的患者。西医多诊断为“局限性肠炎”,但治疗效果有限。一位老支书便血五年,身体瘦得皮包骨,李佃贵仔细观察其舌苔黄厚黏腻,判断其病非单纯脾虚湿盛,而是有毒邪壅结之象。他尝试以黄连、白头翁清热解毒,佐以土茯苓化湿解毒,三个月后,患者体重增加十斤,复查肠镜显示溃疡明显缩小。

“这哪是普通湿热?分明是浊毒胶结!”这一思考促使李佃贵在《伤寒论》中深入研读“瘀热在里”的相关条文,并由此提出“浊毒致病论”——他认为克罗恩病的核心病机并非单一的湿热、虚寒,而是“湿热酿毒,浊瘀阻络”,即病邪与代谢废物在肠道长期交织、胶结、堆积,形成一种慢性毒邪,反复侵犯肠黏膜。
1982年,李佃贵发表《浊毒论治慢性腹泻》,首次系统阐述“浊毒病因学”,一石激起千层浪,成为国内中医界首次正面回应克罗恩病的原创理论。
90年代初,李佃贵接诊了一位从美国回国求医的华裔少女。女孩腹泻日夜不停,一天如厕二十多次,面色苍白、双眼无神,长期激素治疗未见效,母亲抱着病历哭道:“她已经不敢去上学了。”李佃贵深感焦急之下,创造性地提出“三阶段治疗法”:

急性期以化浊解毒为主,采用黄连、苦参、败酱草“以苦坚肠”,并辅以青黛、白及灌肠,收敛止血,保护黏膜;缓解期着重健脾祛湿,选用参苓白术散加土茯苓、穿山龙,以固本清源;稳定期则转入养正防复,开出黄芪、乌梅、石榴皮膏方,扶正固肠、重建屏障。
在根据疗程治疗九个月后,患者症状完全缓解,肠镜显示溃疡面愈合,肠黏膜恢复健康。此案例被收录入《世界疑难病案集》,李佃贵因此被誉为“东方肠病克星”。
2003年,李佃贵带领团队通过基因检测发现:克罗恩病患者体内的TLR4基因多态性与“浊毒症”高度吻合。这一发现为中医“浊毒致病”理论提供了现代分子层面的解释:所谓“浊毒”,实质上是肠道菌群紊乱后引发的低度慢性炎症状态,结合中医湿热、瘀毒、虚损之说,科学与传统实现了桥接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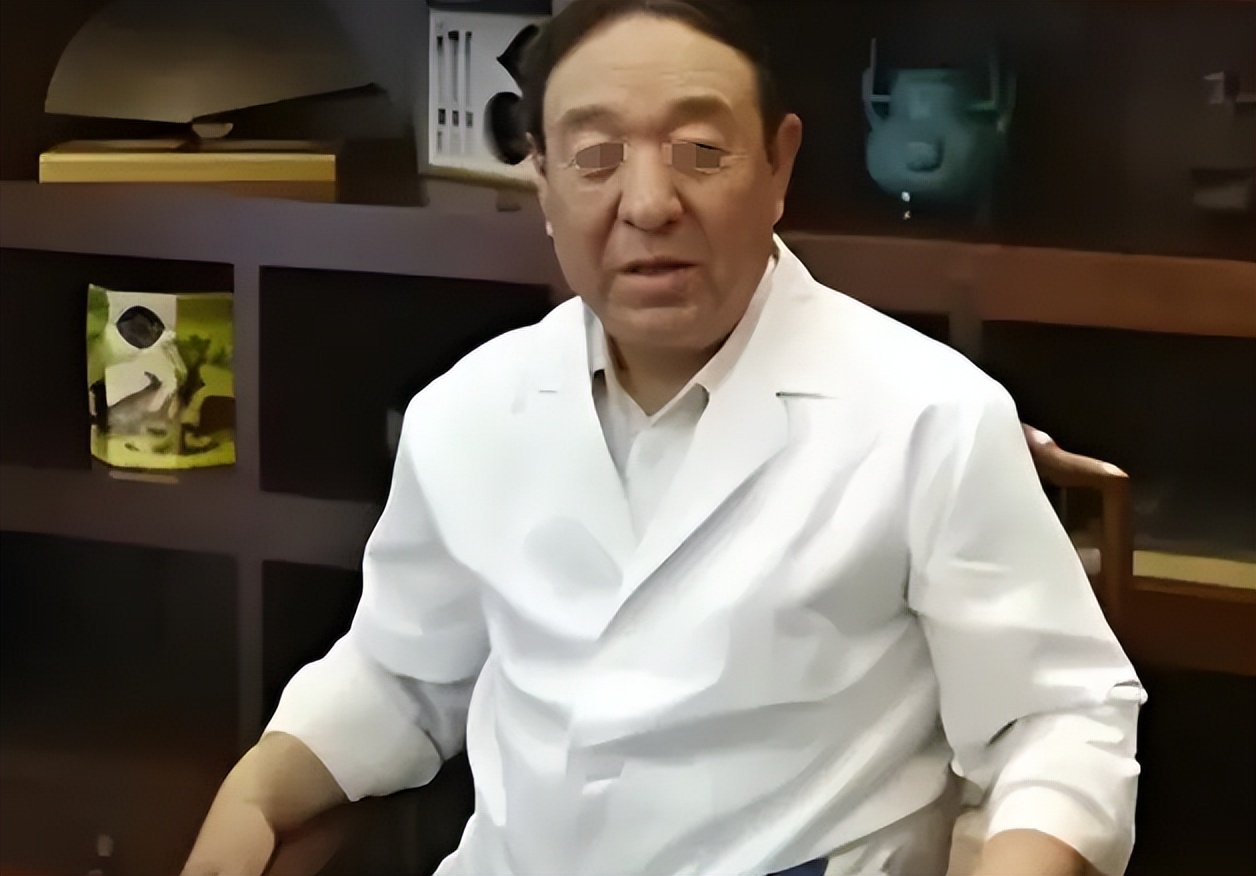
在多年临床实践中,李佃贵总结出“辨浊毒三要素”:一望舌,舌苔黄厚黏腻如油涂;二察便,排出物黏液脓血、状若烂鱼肠;三切脉,脉滑数中带涩象,多见瘀热兼毒之象。一位来自日本的患者服用他研发的“浊毒清”三个月后复查肠镜,医生惊呼:“溃疡面长出了玫瑰红一样的新黏膜!”该案例被日本NHK电视台拍摄为专题纪录片,也推动“浊毒清”成为首个在日本获得特别审批的中药方。
2018年,在罗马召开的世界胃肠病大会上,68岁的李佃贵登台展示“针灸诱导黏膜修复技术”:他现场取足三里、上巨虚等穴位,通过电针调节肠道微循环与免疫调节,肠镜实时监测显示肠道血流量提高近40%。来自欧美的专家对中医“以针调肠”赞叹不已。
如今,李佃贵门下弟子遍布全球32个国家,他创立的“浊毒理论国际研究中心”落户河北中医学院,成为中西医结合治疗肠病的重要基地。即便年逾七旬,李佃贵依旧每周三亲自带教查房,亲手示范“李氏腹诊法”:他用三指沿结肠走向触诊,从回盲部起步,感知肌肉紧张度、压痛点、皮温变化,可准确判断病变区域。

而在近五十年的临床生涯中,李佃贵也始终强调:克罗恩病并不是单纯的“肠子发炎”那么简单。它背后往往不是一个器官的孤立问题,而是一场牵涉脾胃、肝胆、气血、情志的系统性失衡。他常说:“肠为六腑之腑,外泄为主;一旦腑气不畅、湿热夹瘀、毒邪内陷,日久必损正气。治肠,不能只清热止泻,而要三分攻邪,七分扶本。”
在一次国际消化道炎性疾病研讨会上,一位外籍专家提出疑问:“李教授,中医讲‘调理’,但面对克罗恩这种反复发作、久治不愈的慢病,调理真的顶得住吗?”现场气氛一度紧张,很多人以为李佃贵会以学术语言回应,谁知他语气平静却铿锵地说道:
“调,是最深的治。克罗恩病不是‘治好一次’的病,而是‘调一生’的病。不是杀菌消炎就万事大吉,而是要从源头疏浊排毒、固肠养正、调脏通腑。就像你有一条堵塞的河流,你可以每次去捞垃圾,但如果你不解决水源不洁、岸边塌陷、涵洞堵塞的问题,那永远只是治标。”

李佃贵顿了顿,看向满场来自不同国家的听众,补充说道:“其实很多患者一听中医,就问‘多久见效’,‘吃几副药能好’?可我告诉你,克罗恩这个病,哪怕西药见效快,也只是把火压下去,根还在。真正要让肠道恢复自愈力,除了按时吃药、清淡饮食、早睡早起外,你还必须做好三件‘看似简单、实则关键’的事!只要持之以恒,自然会控制好肠道炎症,不仅少动刀子,寿命也完全能和正常人无异!”
“第一件事,是‘守口’——也就是守住吃进肚子里的每一口。”
李佃贵认为,克罗恩病的核心是肠道慢性炎症,而炎症最怕的,就是刺激与波动。他常对患者说:“你的肠子就像烫伤的皮肤,正在结痂愈合,一点点辣、冷、生硬的东西,就会把它撕开。”
因此,他强调饮食不是调理的一部分,而是核心中的核心。真正有效的饮食方案,是“不让肠子受二次伤害”。这意味着,患者必须戒除生冷辛辣、油腻厚味,避免过多蛋白与乳制品,采取少食多餐、温软清淡的原则。米粥、山药、红薯、南瓜、白萝卜等容易消化又有补气养肠作用的食物,是他反复推荐的“肠道修复食单”。
除了忌口,他还推崇“饮食日记”。“每个人的体质和耐受都不一样,什么该吃、什么不能碰,要靠你自己和身体慢慢对话。”有位患者在他的建议下坚持记录三个月,发现自己对牛奶极其敏感,而对燕麦却能良好吸收,从此肚痛腹泻大减。

“第二件事,是‘养心’——这是最被忽略、却最容易导致复发的根。”
李佃贵指出,克罗恩病多发于青壮年,这个年龄段承担着生活、学业、婚姻、家庭等多重压力,情绪紧张、焦虑易怒、抑郁无助等心理波动,极易诱发肠道功能紊乱。
中医有句话:“怒则气上,思则气结,忧则气沉,惊则气乱”,而气机一乱,肠道就首当其冲。李佃贵甚至指出,有不少患者不是因为吃错东西而复发,而是因为“生了一场闷气”。
为此,他特别设计了三步“养心法”:第一,每日自问三句——“今天我哪件事最焦虑?”、“我是否对人憋了情绪?”、“我该怎么调整看法?”;第二,每周做一件让自己开心的小事,如散步、园艺、画画、泡脚;第三,每月至少和一位可信任的人深聊一次,把心里的结打开。
他曾有一位患者,刚入职不久就因上司苛责导致病情爆发,在他指导下调整情绪结构后,后续一年多无明显复发。

“第三件事,是‘顺时’——也就是跟着自然节律生活,让身体自己修好自己。”
李佃贵坚信,人的身体不是靠药治好的,而是靠自我修复能力慢慢修好的。而这个能力,来自于是否“顺应天时”。
克罗恩病患者的肠道屏障功能脆弱,需要夜间肝肾统血、脾胃歇息,来完成黏膜细胞的修补。他总告诫患者:“晚上十一点前一定要上床,不能刷剧刷手机,不然再好的药都白吃。”
他鼓励患者养成早睡早起、按时三餐、日中稍憩的生活节奏;清晨可用艾灸神阙穴助阳,中午可闭目养神15分钟,晚上泡脚后静坐10分钟,有条不紊地让身体代谢、气血流转。
他强调,克罗恩病的关键在于“养病养人,治病治心”。吃药只是外在调控,真正持久的疗效,要靠病人自己的生活配合与自律养生。
许多被多次诊断为“无法逆转”的重症患者,经他三法并行调理一年后,黏膜愈合,症状缓解,甚至十年未复发。李佃贵说:“不是我有什么神药,而是他们真正做到了‘三事不废’。”
他把这套方法总结为八个字:“守口、养心、顺时而行”,挂在河北中医学院的病房墙上。他说,这不是治病的口号,而是每个克罗恩病患者的自救地图。“你只要走在这张图上,不跑偏、不焦急、不中断,病自会止,肠自会安,人也会重生。”
资料来源:
[1]包春辉,黄锦,朱欣怡,等.基于“少阳为枢”探讨针灸治疗克罗恩病的思路[J].中医杂志,2025,66(10):1017-1022.
[2]胡旻萱,王玉丰,李云涛,等.间充质干细胞对克罗恩病合并瘘管疗效的meta分析[J/OL].中华全科医学,1-7[2025-05-27]
[3]范玲燕,詹淑惠,戴莲,等.以肛瘘为首发症状的克罗恩病的诊治研究进展[J].结直肠肛门外科,2025,31(02):106-111
(《国医李佃贵分享:做好这三件事,克罗恩病患者就能控、能稳、能长寿!》一文情节稍有润色虚构,如有雷同纯属巧合;图片均为网图,人名均为化名,配合叙事;原创文章,请勿转载抄袭)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