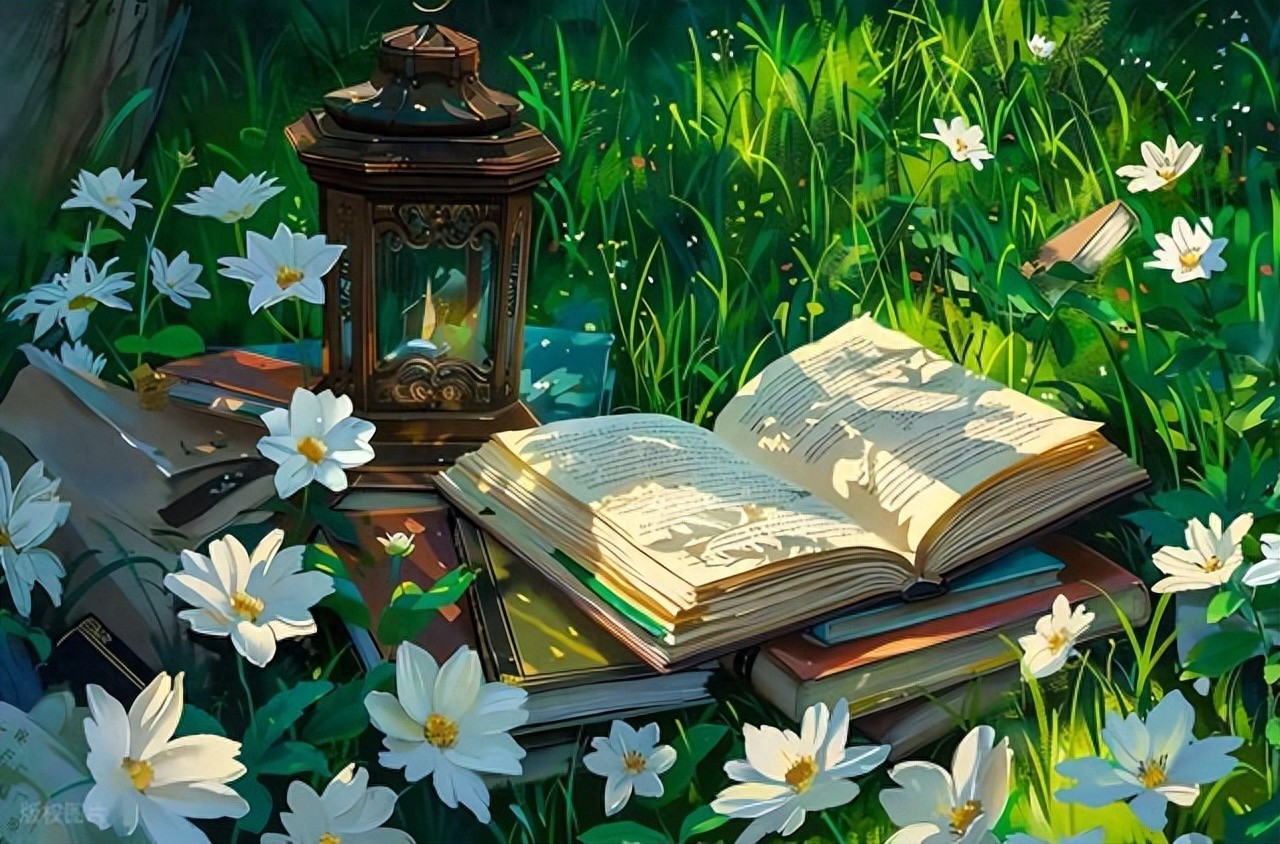
我接触唐诗的时间很早,也可以说我的诗教开始得很早。整个学历教育,从小学到高中,我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完成的。五年制小学,两年制初中,两年制高中。
三年级的时候,来了个新老师,姓汪,经常念小说给我们听。在他的课堂上,激发了我读课外书的愿望。我爷爷上过初小,我父亲上过高小,楼阁上存着几本书。周末的时候,我到楼上找书看。在佛经中夹着一本《绘图千家诗》,一诗一画。
书的扉页是唐代金昌绪的《春怨》。“打起黄莺儿,莫教枝上啼。啼时惊妾梦,不得到辽西。”后来,我读了许多唐诗,多数忘记了,但这一首,却印象深刻,铭记心中。
我初中时的数学老师,是从城里来的。人长得高大英俊,知识青年。他的寝室里蓄着一架书,有几本小说,几本练习书法的字帖,还有一本唐诗。我给老师借书,他说:“诗不是用来读的,要诵,要背。”
这话我记住了,实践了一辈子。我读诗,抑扬顿挫,把文字还原为声音。后来教学生读诗用的就是这种方法,退休后教我孙子读诗也还是这样。书读百遍,其意自见。熟悉了,会背了,就会应用,触景生情,出口成章。
在这本书上,我学习了杜甫的“三吏”“三别”,白居易的《长恨歌》,李商隐的《无题》诗。一个人在竹林里下功夫背诵“车辚辚 马萧萧,行人弓箭各在腰……”还有李白、李贺、王维的诗。在反复读背的过程中,我对唐诗建立起印象。
上世纪八十年代,文化解冻。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文学小丛书,不大,可以装在衣袋里。我买了《宋词一百首》、《元曲一百首》,常放一本在口袋里。放学回家的路上,把读过的宋词翻出来,想一想,记一记。
春天,好风飘飘,我在乌桕林里吟诵;夏天,我在月光下吟诵;秋天,枫叶红了,牵牛花开,我在土崖前吟诵;冬天,漫漫长夜,我躺在床上,在心中吟诵:
“更深月色半人家,北斗阑干南斗斜。今夜偏知春气暖,虫声新透绿窗纱。”
“君自故乡来,应知故乡事。来日绮窗前,寒梅著花未?”
“月黑雁飞高,单于夜遁逃。欲将轻骑逐,大雪满弓刀。”
“花褪残红青杏小。燕子飞时,绿水人家绕。枝上柳绵吹又少,天涯何处无芳草!”……
有一年,班上举行唐诗宋词擂台赛。学生背一首诗词,我背诵一首。学生多背,老师也要跟着多背。全班三十多个学生。我事先做好准备,翻检记忆的仓储,背诵、统计,得到结果是,我能背出三百多首唐诗宋词。
少年读诗,中年读词,老年读唐诗宋词。熏陶感染,我的精神底色被古典诗词涂抹得异常鲜明,是这些文化奇葩装点了我的心灵世界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