"我得回去了。"女婿秦志国站在门口,眼神飘忽,这句话像一块石头,沉甸甸地砸在我心上。
早春的阳光透过褪了色的碎花窗帘,斜斜地洒在客厅磨得发亮的地板上。
我正蹲在小火炉旁给外孙小杰热牛奶,听到这话手一抖,差点把搪瓷杯子打翻。
"回哪去?"我装作没听明白,手上继续搅动着牛奶。
厨房里飘来阵阵葱花炒蛋的香气,那是我天不亮起来特意给小杰做的早餐。
十年前,当女儿小雪打电话说生了个男孩,让我从乡下赶来帮忙带孩子时,我二话没说就收拾行李来了。
那时候是1995年,我刚满52岁,本想在老家的田里种点蔬菜自给自足,安安稳稳过日子。
小雪的电话是在乡邮局打来的,邮局主任老李扯着嗓子喊:"刘大姐,你闺女电话!"
我放下手里的菜篮子,一路小跑过去,听筒里传来女儿哭腔:"妈,我生了,是个男孩,我和志国都得上班,没人照顾孩子..."
第二天,我就坐着绿皮火车,带着一篮子老家的鸡蛋和玉米面,来到了这个陌生的城市。
秦志国当时刚在单位评上副主任,小雪在新开的商场做销售主管,两人忙得不可开交。
我这个只认得几个字的农村老太太,就这样成了他们的救星。
"秦志国,你再说一遍?"女儿小雪从房间里冲出来,脸色发白。
她穿着工作服,头发还没来得及梳,手里拿着半截面包。
"我爸要来城里养老,这不,咱们这房子就三个卧室,外公来了,总得腾个房间吧。"
秦志国的声音不高不低,仿佛在说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。

我手里的牛奶杯终于搁到了桌上,心里却像滚开的水锅,咕嘟咕嘟冒着泡。
十年了,从小杰呀呀学语到如今上小学四年级,这孩子每一寸成长都有我的影子。
记得他刚出生那会儿,小小的一团,哭起来嗓子眼像打了结的铜喇叭。
乡下人带孩子自有一套,我用小米粥煮得稀烂,放凉了一点点一点点地喂;冬天给他洗澡,用旧床单围成一圈,生一盆炭火在旁边取暖;他肚子上起的疹子,我用热毛巾敷;晚上睡不好,我就轻轻拍着,哼着家乡的小调:"摇啊摇,摇到外婆桥..."
如今这样的日子,竟要被一句话打发回乡下的老屋?
"外婆不走!"小杰突然放下筷子,扑到我怀里,小手紧紧抓着我的粗布围裙,"你走了,谁给我叠千纸鹤?谁教我写毛笔字?谁陪我去放风筝?"
当年那个满脸稚气的小不点,如今已经是个瘦高的小伙子了。
我摸着他的头,心里又酸又涩,又不想让孩子看出我的难过,只能使劲眨眼睛。
电视机里正播放着早间新闻,八点整的钟声敲响了。
小雪咬着嘴唇,眼眶红红的:"妈,你先别急,我再跟他商量商量。"
秦志国皱了皱眉:"还有什么好商量的?一家人还能不管老人家?"
说完,他拿起公文包,头也不回地出了门。
那天晚上,我躺在小杰房间的折叠床上,翻来覆去睡不着。
想起十年前刚来时,秦志国还曾抱怨我做饭太咸,洗衣服不分类,让他在同事面前没面子。
那时我差点收拾包袱回老家,是小雪劝我:"我妈就这水平,您凑合着吃吧,再说孩子还小呢。"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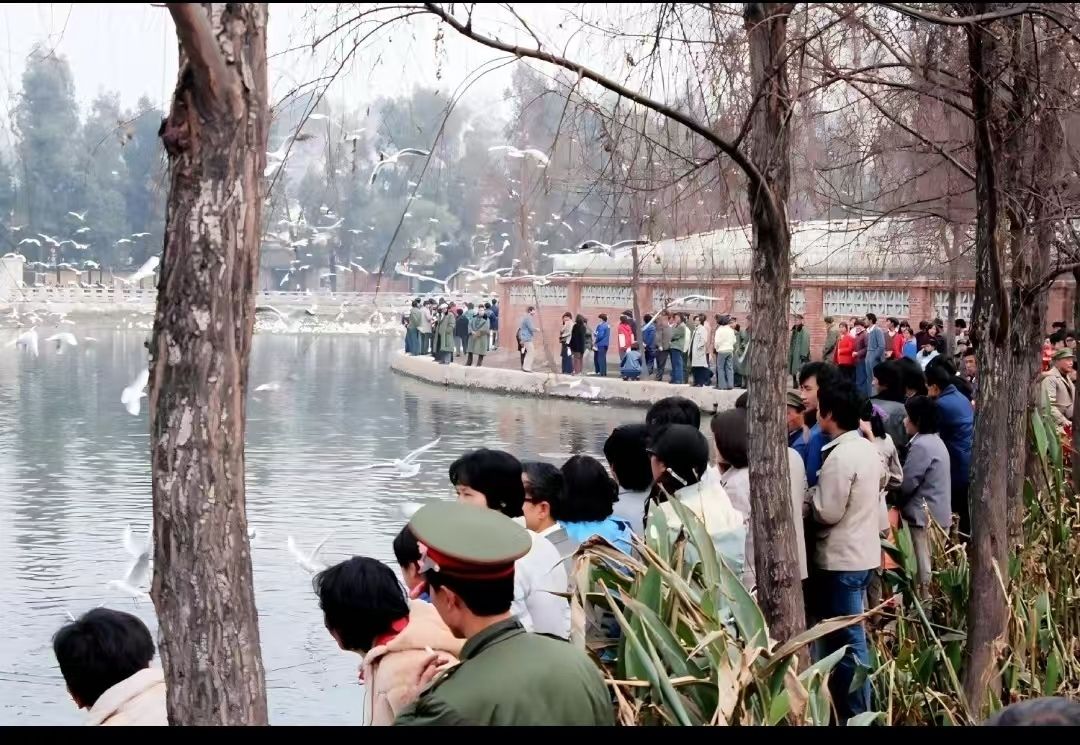
十年里,我学会了用电饭煲,买了人生第一部老人机,背下了小杰学校的作息时间表,甚至学会了在菜市场讲价还价。
我以为,我已经成了这个家不可缺少的一部分。
墙上的老式挂钟嘀嗒嘀嗒地响,隔壁小杰的呼吸声均匀平稳。
窗外,城市的霓虹灯一盏盏熄灭,只剩下马路对面通宵营业的小卖部亮着惨白的灯光。
我拿出枕头下的老照片,那是我和老伴在老家门前的合影,照片已经泛黄,边缘还有些卷曲。
老伴走得早,留下我一个人在乡下的老房子里,十年前小雪生产,算是给了我新的寄托。
我叹了口气,把照片放回去,轻轻擦了擦眼角。
第二天,亲家公秦老汉来了,拖着一个老式的蓝格子行李箱,背有些驼,但精神还算硬朗。
"弟妹,多年不见啊,你这身子骨倒是结实。"他笑呵呵地对我说。
我勉强挤出一丝笑容:"亲家,您老身体还好吧?"
"哎,老毛病,高血压,冠心病,天天吃药,能咋样?"秦老汉叹了口气,"还是城里好啊,医院方便,孩子们也能照应着。"
小雪忙着收拾客房,把原本属于我的那间屋子腾了出来。
我的东西不多,一个旧皮箱就装完了,连同这些年给小杰织的毛衣,都整整齐齐地叠好。
"妈,您先别着急回老家,再住几天,看看情况再说。"小雪趁秦志国不在家,悄悄对我说。
亲家公来了以后,家里气氛变得微妙。
早上六点,我习惯性地起床准备早饭,却发现亲家公已经在厨房忙活了。

"弟妹,我来弄就行,你歇着吧。"他手里拿着锅铲,显得有些笨拙。
我只好退出厨房,坐在客厅的沙发上,感觉浑身不自在。
秦老汉是个倔脾气的东北人,腿脚不便却坚持自己做饭。
他做的饭和我不同,爱放葱姜蒜,油大火大,整个房子都是呛人的油烟味。
小杰偷偷跑来对我说:"外婆,外公做的饭不好吃,我想吃你做的蒸蛋。"
有一次,秦老汉在厨房笨手笨脚地切菜,锅里的油烧得冒烟,差点酿成火灾。
秦志国大发雷霆,父子俩顶了一顿嘴。
"你少管我!"秦老汉拍着桌子,"我一辈子没伺候过人,现在老了还得看你脸色!"
秦志国也不甘示弱:"您老也不看看自己什么情况,膝盖疼得连楼都下不去,还逞什么能!"
我站在一旁,不知道该劝谁,心里更加不是滋味。
这个家,渐渐没了我的位置。
小杰的学习也开始走下坡路。
以前我每天接送,风雨无阻,放学在校门口等着,手里总拿着热乎乎的红薯或者刚炸好的麻花。
检查作业时,我虽然不认识多少字,但会一笔一画对着课本认真看,确保他做完了每一题。
现在亲家公年纪大了,记性也不好,常常忘记接孩子,有一次小杰在校门口等到天黑,是班主任张老师送他回来的。
。
"小杰最近成绩怎么下滑这么多?"有一天晚上,秦志国翻看小杰的试卷,皱着眉头质问。
"别人都有家长辅导,我没有。"小杰低着头,声音很小。
"你爷爷不是在家吗?"秦志国问。
"爷爷只会讲东北的老故事,作业都不会..."小杰话没说完,就被秦志国打断了。

"没大没小,怎么说话呢?"秦志国扬起手,吓得小杰一缩脖子。
我在一旁看不下去了:"志国,孩子说的是实话,你又何必..."
"妈,您就别管了!"小雪连忙制止我,怕引起新的争执。
我闭上嘴,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,酸甜苦辣咸,说不出是什么滋味。
那天晚上,我收拾了简单的行李,执意要回老家。
"妈,您别走啊,小杰还等着您辅导作业呢。"小雪拉着我的手。
"算了,我这老婆子,也该回农村了,城里不是我呆的地方。"我故作轻松地说。
其实这些年,我也攒了点钱,准备给老家的房子翻修一下,补补漏雨的屋顶,换几扇新窗户。
回到老家的第一个星期,我就像丢了魂似的,白天在院子里晒太阳,夜里听着远处火车的汽笛声,想着城里的小杰。
农村冬天的夜特别长,特别冷,特别静。
我的邻居王婶看不下去了,常来陪我说话:"刘大姐,你这是想孙子想魔怔了?要不我陪你去城里看看?"
我摇摇头:"不去了,人各有命,强扭的瓜不甜。"
可心里却像有只猫爪子在抓,总想着小杰的功课怎么样了,有没有穿够衣服,晚上盖没盖好被子。
一个月后的一天,我正在院子里劈柴,忽然看见村口停了一辆出租车。
小杰从车上跳下来,一路小跑过来:"外婆!外婆!我想死你了!"
身后跟着小雪,手里提着大包小包。
"你们怎么来了?"我又惊又喜,连忙放下斧头。
"妈,小杰放寒假了,我请了两天假,带他来看看您。"小雪说着,把手里的东西放下,是些城里的点心和水果。

院子里劈好的柴火整齐地码着,墙角还有我种的几盆菊花,已经开得很旺。
小杰一进屋就东瞧西看:"外婆,你这房子好破啊,下雨会漏吗?"
"傻孩子,你外婆住了大半辈子的房子,比城里那水泥盒子舒服多了。"我笑着拍拍他的脑袋。
晚上,我做了一大桌子家乡菜,红烧肉、酸菜鱼、炖鸡、拌野菜,都是小杰爱吃的。
我特意用柴火灶烧的水煮的茶,香气四溢。
小杰吃得满嘴油光:"外婆,你做的菜还是最好吃!"
吃完饭,小雪帮我收拾碗筷,欲言又止的样子。
我问:"有啥事就直说吧,这么多年了,还跟我客气?"
小雪叹了口气:"妈,家里的情况越来越复杂了。爸爸的血压控制不好,前两天差点犯了心脏病,吓得志国赶紧请了假,带他去医院检查。"
我手上的动作停了一下:"怪不得今天没见志国来。"
"他在医院陪我爸呢。"小雪低着头,"妈,其实他不是不尊重您,只是..."
我打断她:"我懂,自己的爹妈都想顾,哪有两全的事?"
小雪红了眼眶:"妈,您别这么说。志国其实很感激您这些年的付出,只是他不善表达。"
"是吗?"我有些不信。
小雪继续说:"有一次,他喝多了,跟我说他这辈子欠您的情,将来一定要报答。"
我笑了笑:"他能好好待你和小杰,就是报答我了。"
夜深了,我和小雪坐在炕上,小杰已经睡着了,发出均匀的呼吸声。

我们母女俩说了很多话,从她小时候的趣事,到我和她爸爸的往事,再到小杰的成长。
"妈,我跟你说个事。"小雪犹豫了一下,"其实去年村里修的那条路,是志国出的钱。"
我一愣:"啥?"
"他去年过年来看您,发现村里的路下雨天全是泥,很不方便,回去就联系了村长,出资把主干道都修了,但不让我告诉您,说怕您心里不好受。"
我听了又惊又疑:"这事儿我怎么不知道?"
第二天,我偷偷去找村长王大明。
他一见我就热情地招呼:"刘大姐,今儿个啥风把你吹来了?"
我单刀直入:"听说我们村的路是我女婿出钱修的?"
王大明点点头:"可不是嘛!去年五月,你女婿来我家,二话不说拍了两万块钱在桌上,说是为了你老人家方便,把村里的主路修一修。"
"他还说啥了?"我追问。
"他说这是他应该做的,让我们保密,别告诉你。"王大明挠挠头,"这事儿都快一年了,怎么突然问起来了?"
我没回答,心里像打翻了蜜罐子,甜滋滋的。
回家路上,我看着平坦的水泥路,想象着秦志国当初来村里的情景,不由得眼眶湿润。
原来,他背地里还惦记着我这个乡下老太太的生活。
一天放学后,我从老家赶来看小杰,正巧听见秦志国在电话里急得直跺脚:"我爸血压又高了,这已经是这个月第三次了,我这工作走不开,你能不能请个假回来?"
原来,亲家公的身体状况很不好,秦志国请他来城里,主要是为了就近照顾。
这个平日里看起来有些冷漠的女婿,也有他的难处。

想到这里,我心里的那根弦松了下来。
许多事情,站在不同的位置看,感受全然不同。
我也有父母,知道赡养老人的不易;我也曾是儿媳,知道平衡婆媳关系的艰难。
如今我在秦志国家的地位,不就是当年我婆婆在我家的处境吗?
想通了这一点,我决定主动减轻他们的负担。
小杰和小雪回去后,我开始着手收拾老屋。
用存了多年的积蓄,请村里的木匠换了几扇窗户,刷了新漆,又买了一台二手的彩电。
日子一天天过去,我渐渐适应了独居的生活,每天种点菜,养几只鸡,闲时到村里老姐妹家串串门,日子也过得充实。
可每到夜深人静,想起小杰那双渴望的眼睛,心里还是空落落的。
六月的一天,天刚蒙蒙亮,我就听见院外有汽车喇叭声。
揉着睡眼走出去,发现秦志国的车停在门口。
"妈,我来接您。"秦志国从车上下来,神情有些局促。
"接我?去哪?"我一头雾水。
"回家。"秦志国说,"小杰整天念叨您,连饭都吃不好了。"
我心里一暖,但还是摇摇头:"你爸不是身体不好吗?我去了添什么乱?"
秦志国叹了口气:"我们想通了,家里地方虽小,但挤一挤还是住得下的。"
看我还在犹豫,他又补充道:"不是让您回原来那屋,小雪找了个新地方。"
我将信将疑地跟他上了车。
一路上,秦志国少有地健谈,说起了这些年工作上的事,还问我对市场上的蔬菜价格有什么看法。
到了城里,车子没往他家的方向开,而是拐进了一个我从没去过的小区。

"这是哪?"我问。
"到了您就知道了。"秦志国神秘地笑笑。
电梯停在五楼,秦志国掏出钥匙,打开了一扇门。
小雪和小杰早已等在里面,一见我进来,小杰就像离弦的箭冲过来:"外婆!我就知道您会来!"
我环顾四周,这是一套不大但很整洁的两居室,客厅里的家具简单但齐全,墙上还挂着我们全家的合影。
"这...这是哪?"我再次问道。
小雪神神秘秘地拉着我去看了书房和卧室,然后说:"妈,这是给您租的房子,就在我们家小区旁边,离小杰的学校也近,您想来看小杰随时都行,又不耽误爸爸照顾公公。"
我站在陌生的客厅里,从窗口就能看到小杰的学校。
心中的委屈和不舍,在阳光下慢慢化开。
"这租金得多少啊?"我下意识地问,乡下人的节俭习惯让我担心增加他们的负担。
"妈,您就别操心这个了。"小雪笑着说,"志国单位发了福利分房,这套是他用工龄换来的,本来准备出租的,现在给您住正好。"
我看向秦志国,他难得地露出一丝腼腆的笑容:"妈,您这些年辛苦了,小杰能有今天,全靠您啊。"
那一刻,我的眼泪再也控制不住,夺眶而出。
"我想通了,"我对小雪说,"你们都不容易。"
"妈,我..."小雪抱住我,眼泪掉了下来,"这些年您操心的事太多了。"
后来我搬到了新家,每天早上还是去接小杰上学,晚上把他送回家,然后自己回到安静的小屋。
有时候亲家公的血压不稳,我也会去帮忙做饭收拾。

秦老汉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,对我也多了几分敬重:"弟妹,你这心胸,比我宽广多了。"
我笑着说:"都一把年纪了,计较那么多干啥?能看着孩子们好好的,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。"
秦志国难得地在一个周末来看我,带了一盆我爱种的菊花,黄橙橙的花朵在阳光下格外耀眼。
他站在门口局促不安:"妈,你看这盆花...适合放阳台吗?"
透过他蹩脚的问候,我看到了未曾表达的敬意。
我接过花盆,放在阳台的正中央:"适合,很适合。"
阳光透过花瓣,在地板上投下斑驳的影子,像极了我们这些年的关系,有明有暗,却始终连在一起。
天下没有不老的父母,也没有不长大的孩子。
沧海桑田中,我们各自挣扎,各自妥协,却都在尽力维系那根亲情的线,让它不至于在岁月中断裂。
小杰上初中了,我依然每天去学校门口等他。
他个子蹿得很快,已经比我高了大半个头,背着书包走在前面,我就慢慢地跟在后面。
有一次,他问我:"外婆,你为什么总是帮我们?爸爸妈妈对你不好的时候,你都不生气吗?"
我笑着回答:"傻孩子,哪有那么多生气不生气的?人这一辈子,就是过日子,日子里有酸有甜有苦有辣,尝尽了百味,才算活明白了。"
小杰似懂非懂地点点头。
回到家,我从柜子里翻出那张老照片,我和老伴在老家门前的合影。
如今照片已经泛黄,但里面的笑容依然清晰。
我轻轻擦拭着照片上的灰尘,喃喃自语:"老头子,你看,咱们的日子,总算过出了点模样。"

窗外,夕阳西下,晚霞染红了半边天。
城市的灯光一盏盏亮起,勾勒出这座城市的轮廓。
这大概就是为人父母的宿命——再深的爱,也要学会在适当的时候放手,给彼此留出成长的空间。
毕竟啊,儿行千里母担忧,天下父母心,终究都是一样的。
而那些生活中的磕磕绊绊,不过是岁月长河中的一朵小小浪花,终将在时光的冲刷下,化为平静的水面,映照出我们共同的倒影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