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医经钩考》五十五、漫谈中医十二官:膻中(心包)
——臣使与卫尉之官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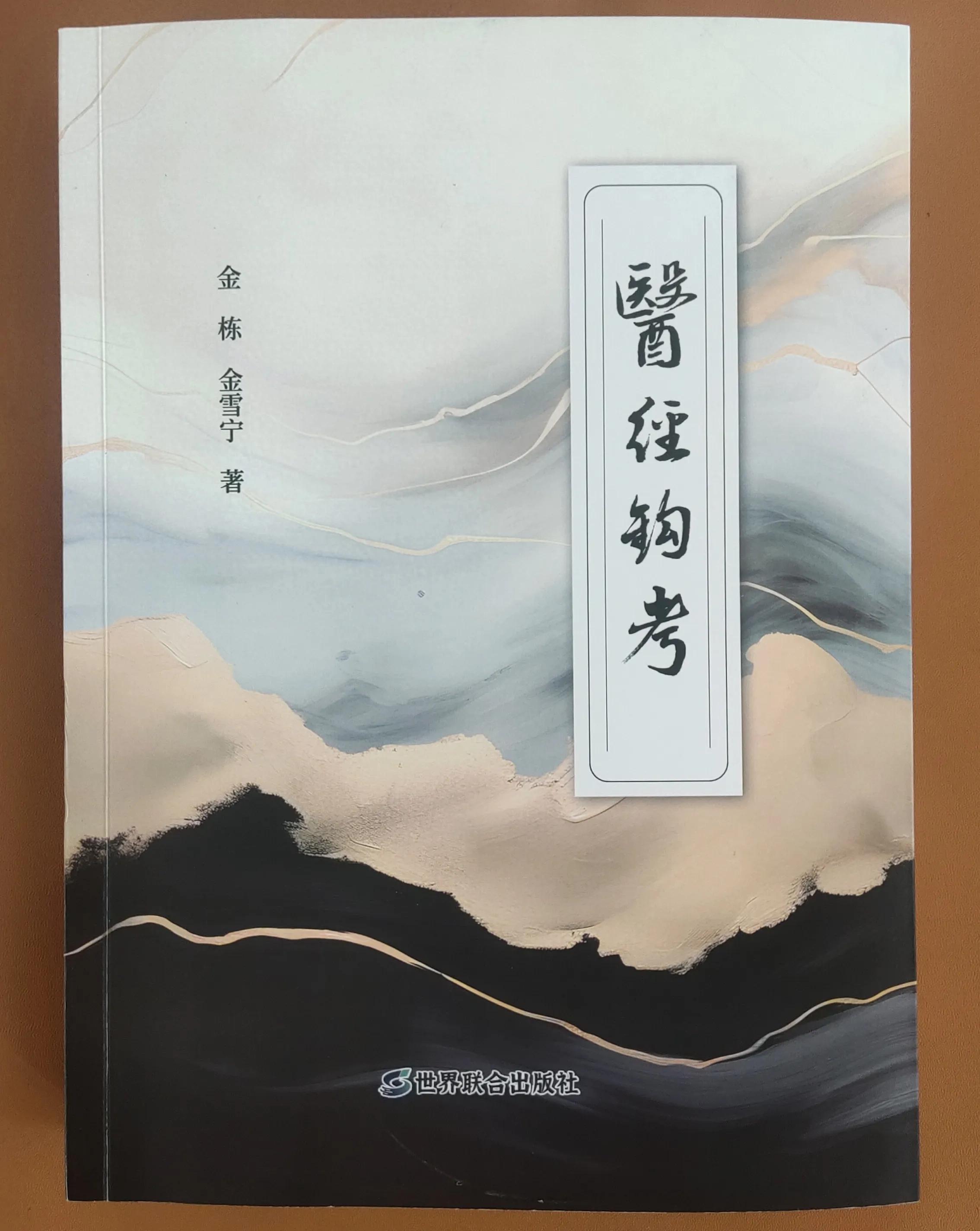
以上五脏官职,多是中央行政官府之官称,《千金方》俱载,在六脏官职中,无“膻中-心包”之说。因汉代官典《白虎通》系称“五脏六腑”,一直流传至今。如《白虎通·性情篇·五脏六腑主性情》说:
“五脏者,何也?谓肝、心、肺、肾、脾也……六腑者,何谓也?谓大肠、小肠、胃、膀胱、三焦、胆也。”
《白虎通·性情篇·论五性六情》说:
“性所以五,情所以六何?人本含六律五行之气而生,故内有五脏六腑,此情性之所由出也。”
孙思邈不认同膻中这一脏,在书中多是五脏六腑并提,并不言及膻中。如《千金方·卷十一·肝脏脉论第一》说:
“论曰:夫人禀天地而生,内有五脏、六腑、精气、骨髓、筋脉,外有四肢、九窍、皮毛、爪齿、咽喉、唇舌、肛门、胞囊,以此总而成躯……所以此之中秩,卷卷皆备述五脏六腑等血脉根源、循环流注,与九窍应会处所,并论五脏六腑等轻重大小、长短阔狭、受盛多少……凡五脏在天为五星,在地为五岳,约时为五行,在人为五脏。五脏者,精神魂魄意也。”而《素问·灵兰秘典论》则说:
“膻中者,臣使之官,喜乐出焉。”
张介宾《类经三卷·藏象类一》说:
“膻中在上焦,亦名上气海,为宗气所积之处,主奉行君相之令而布施气化,故为臣使之官。《行针篇》曰:‘多阳者多喜,多阴者多怒。’膻中为二阳脏所居,故喜乐出焉。按十二经表里,有心包络而无膻中。心包之位正居膈上,为心之护卫。《胀论》曰:‘膻中者,心主之宫城也。’正合心包臣使之义,意者其即指此欤?”
张志聪《素问集注》说:
“膻中者,心主之宫城,心之包络,位居膻中,而代君行令,故为臣使之官。心志喜,心主代君宣布,故喜乐出焉。”
高士宗《素问直解》说:
“膻中,即心包络。心包代君行令,犹之臣使之官,宣通络脉,故喜乐由之出焉。”
胡天雄《素问补识》说:
“膻中本有二义,一为气海,在胸腔。《灵·海论》‘膻中者,为气之海’即是,两乳之间的膻中穴,就是根据这个膻中命名的。一指心包络,即心的外围组织。《灵·胀论》‘膻中者心主之宫城也’即是,此处膻中是包络不是气海……喜为心志,心所喜乐,由膻中传出,所以说‘喜乐出焉’并非膻中本身发出喜乐。”
傅景华《黄帝内经素问译注》说:
“膻中:《灵枢·胀论》:‘膻中者,心主之宫城也。’此指心包络。臣使:指君主的使者,代表其行使某些职能。”
臣使之官:使,《简明中国历代职官辞典》说:
“官称。愿意为受命出使者。南北朝时,高级官员执行临时任务,偶以使为名,如北魏以郦道元为大使尉抚六镇等。唐中期以后,以使名官者渐多,如节度使、盐铁使等,故诏令常以诸司诸使概括国家机构。”
观明清温病学说,或云“心包者,卫尉之官,代心受邪”,以补《千金方》十二官之数,未知可否?
清·叶天士《温热论》说:
“温邪上受,首先犯肺,逆传心包。”
新世纪第二版高校教材孙广仁主编《中医基础理论·第三章藏象·第二节五脏》说:
“附-心包络:心包络,简称心包,亦称‘膻中’,是心脏外面的包膜,有保护心脏的作用,在经络学说中,手厥阴心包经与手少阳三焦经相为表里,故心包络属于脏。古代医家认为,心为人身之君主,不得受邪,所以若外邪侵袭,则心包络当先受病,故心包有‘代心受邪’之功用。如《灵枢·邪客》说:‘心者,五脏六腑之大主也,精神之所舍也。其脏坚固,邪弗能容也。容之则心伤,心伤则神去,神去则死矣。故诸邪之在于心者,皆在于心之包络。’后世明清温病学派受‘心不受邪’思想的影响,在温病学说中,将外感热病中出现的神昏谵语等心神机能失常的病理表现,称之为‘热入心包’或‘痰热蒙蔽心包’。实际上,心包受邪所出现的病证,即是心的病证,心和其他脏器一样,皆可受邪气之侵。”
卫尉者何官职?《简明中国历代职官辞典》说:
“卫尉:官名。秦置,掌率卫士守卫宫禁。汉沿置,秩中二千石,为九卿之一,有丞。景帝初改名为中大夫令,后元年(前143)复原名。东晋不置。南朝宋孝武帝复置。”
附:五脏为何要加上“心包”变为六脏?
五脏六腑四字连用者,《内经》全书共52见,其中《素问》14见,《灵枢》38见。
习惯上称“五脏六腑”,即“肝心脾肺肾”而无“心包”一脏,为什么要加上“心包”又有“六脏六腑”之称呢?只是出于理论需要,据“天人相应”观,为了与三阴三阳(厥阴、少阴、太阴,少阳、太阳、阳明)相合,再配属人体十二经脉之故。即“为了满足阴阳思想的需要,十一经非要变为十二经。于是,添上‘心包’一脏。”(赵洪钧《中西医结合二十讲》)
赵洪钧《中西医结合二十讲》说:
“按说,严格按五行学说建立脏腑模型,就应该是五脏五腑。可是,在中医理论完成的过程中,先后或同时有三种哲学思想起作用。一是阴阳说,二是五行说,三是天人相应说。它们之间有联系,却不是同时出现的。最后,某些道家术语混入。于是,脏腑学说中,出现了多余的构件。多余的结果,不是使理论更圆满细密,相反,它们引起混乱或模糊……
“为什么要五六凑十一呢?这完全是受‘天人相应’思想影响。汉代之前,五六模式可能还没有被视为生命构造的基本模式。到脏腑经脉说创立时,五六思想影响很大。《汉书·律历志》说:‘天六地五,数之常也。天有六气,降生五味。夫五六者,天地之中合,而民所受以生也(洪钧按:此句之意为‘人之所以有生命’)。故日有六甲,辰有五子,十一而天地之道毕,言终而复始也。’于是要说五脏六腑。否则,不够十一,有违天意。
“恽铁樵曾说,干支只是五六,天六地五来路大约如此。读者可能还不明白,天六地五是什么意思。这是从天干地支来。干支二者,干为阳,支为阴。天干本来有十,地支本来有十二。可是,在一甲子(即六十花甲,古人先是用它记日)中,甲出现六次,子出现五次。其中的数学道理本来很简单,因为十和十二的最小公倍数是六十。在这一循环中,天干只能循环六次,地支只能循环五次。古人则认为这是妙不可言的天意。关乎人的生命。所以阳经有六,阴经有五。腑有六,脏有五。不如此就违背天数。”
这就是五脏六腑的最后定型。
《中西医结合二十讲》又说:
“由于‘经脉’最后完成十二经脉说。所以,毫无疑问,心包就是出于十二经脉说的理论需要增加的。心包的前身是什么呢,就是膻中……
“到了《胀论》,膻中和心发生了关系,于是,心包说有了根据。到底是《经脉》篇从《胀论》受到启发,还是后者为前者制造依据,不必深究。但《胀论》是《内经》中唯一使膻中和心包发生联系的一篇是无疑的。从此膻中演变为心包,而且二者并存。《灵枢·营气》也提到膻中,那是十二经脉说完成后的应用。其中没有说膻中是什么。
“《素问·灵兰秘典论》关于膻中的原话是:‘膻中者,臣使之官,喜乐出焉。’由于该篇有‘凡此十二官者,不得相失也’之语,故它很可能是十二经脉说完成之后的产物。
“膻中直接和心包发生关系,还见于《素问·刺法论》这个遗篇。而且,正是从《灵兰秘典论》发挥而来。所以,古人认为《素问·刺法论》不是《素问》原有,是有道理的。该篇说:‘膻中者,臣使之官,喜乐出焉。可刺心包络所流。’这说明该篇的作者,既看过《灵兰秘典论》也看过《经脉》。其作者应该是《内经》基本完成之后才出世的……
“可以看出,添上心包这一‘脏’,只是为了凑够六脏六腑。不然,五脏六腑各一经,只能是十一经。其实,今《内经》至少还有4篇(灵2、41,素36、59)留有明显的十一经痕迹。足见十一经脉保持了很长时间。十一经是对应五脏六腑的。至今我们仍然习惯说五脏六腑。”
